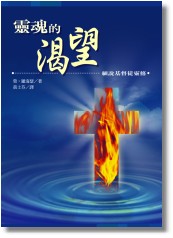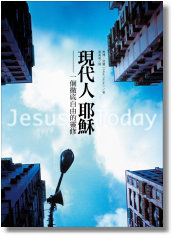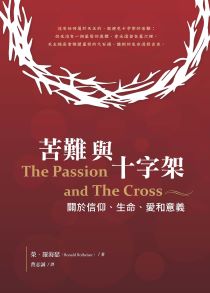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本書目錄
精采書摘
內頁試讀
在忙碌混亂的世界中,我們愈來愈不容易在生活中找到靈修的意義,就連信徒們也時常感覺不到天主的臨在。正如無神論哲學家尼采 ( Friedrich Nietzsche ) 所言,那盞充滿天主臨在之光的燈,已遭摔毀。在《四碎之燈》中,榮‧羅海瑟 ( Ronald Rolheiser )──《靈魂的渴望》作者──觀看無神論者及不信者如何在我們的世界蔓延,以及我們如何在他們的面前重新修補這盞破碎的燈,聚集天主的臨在之光。作者提出克服自戀主義和對成就著迷的方法,不是靠更多的學習和嘗試,而是藉不同的生活方式。保有默觀的生活能夠讓我們再次跟隨天主臨在之光的引領。
相關推薦書籍
榮.羅海瑟(Ronald Rolheiser,1947~)神父,加拿大籍無玷聖母獻主會 (O.M.I.) 會士,1972年晉鐸,1982年取得魯汶大學得博士學位,其專長為靈修學及系統神學。曾任教職,並定期在《天主教前鋒報》(The Catholic Herald) 等數十份刊物發表專欄文章,因其一系列環繞靈修、神學及現代世界等議題的書籍,重新喚醒人對靈修的意識與熱情而聞名。
其中譯著作有:《靈魂的渴望》、《四碎之燈》、《不安的靈魂》、《苦難與十字架》。
作者相關書籍
序言 致謝
第一部 自戀主義,實用主義,難以克制的不安,喪失「驚奇」這份舊時的本能
第一章 信友當中無信的問題
第二章 自戀主義、實用主義、難以克制的不安與喪失默觀性的人格
第三章 全然不同的局面
第二部 恢復對驚奇的舊時本能:西方基督宗教 思想中的三項默觀傳統
第四章 意識的淨化
第五章 欽崇天主神聖的默觀
第六章 了解與接納人的偶存性
第三部 恢復對驚奇的舊時本能:一項具體的實踐
第七章 當代的靈修操練 回顧指引關於作者
第一章 信友當中無信的問題 日常意識中的不可知論 史上最富盛名的小說之一是這麼開始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1。 適用於家庭的這句話,對各個世代而言亦然,每一世代都有它獨一無二的不幸。尤其在宗教掙扎這方面,我們的世代也不例外。以往世代的信友,為教會、 聖經的詮釋,及基督的唯一性和定位等諸多問題,在那裡爭論不休,而我們自身的宗教掙扎卻聚焦在最核心的問題,即天主的存在。 我們活在無信的年代。使我們和以往世代有所區隔的是,今天,無信的問題在有宗教和無宗教者間一樣真實。關於信德的問題,正是信友之間的無信。 相信天主,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幾乎如同南柯一夢。我們還可感覺到以往宗教活動的痕跡,但是我們自身的意識已近於不可知論。在生活的茶米油鹽當中,罕見對天主鮮明的感受。在教堂裡,我們仍為天主安排一席之地,但祂在其他場所則備受限制。 百年前,當尼采宣告「上帝已死」,他不是指天上的神已死,而是說日常生活中,天主已無關緊要了。上帝是死了,尼采又說,但祂的「影子仍舊很長,我們應該首先征服這陰影」2。 當代分析家斐理.萊佛(Philip Rieff)也有類似的說法。以他的觀點,我們的世代與天主的關係曖昧難辨:祂雖已消失不見,但我們仍有一張祂的名片。祂雖然缺席,但因為我們過去的宗教信仰,我們仍保有對祂的一絲感受。未來的世代,他斷言,連這樣的感受也不會有3。 這些意象,談到信仰猶如南柯一夢,談到宗教猶如與天主的陰影掙扎,談到天主雖已不在,但我們仍留著一張名片,約略地描述了我們每天在信仰與不可知論之間的掙扎。我們仍然對天主有些體驗,即便那往往並非直接自活水中飲取的鮮明體驗。就算天主真的進入我們每天的體驗,大半我們所感受的,並非一位活生生的人,我們真的和祂說話,從祂那裡尋求終極的慰藉,就像個人對個人,朋友對朋友,情人對情人,小孩對父母那樣的關係。 相反地,我們經驗天主、談及天主時所想到的,乃是一種宗教、一個教派、一種倫理哲學,道德的指引,尋求正義的必然,或一種社交上的懷舊。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相信天主好比如此:天主就是宗教信仰,而宗教代表的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去教堂、服從聖經、性行為只限於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不可說謊、欺騙或起誓,民主原則、合宜的審美觀、對人要友善。 因此,天主成了某種倫理及思想的原則,而非一個人格。我們對這原則所投注的心力,從可以為之慷慨就義的熱烈情感,轉變成模糊的懷舊心態。在這心態中,天主與宗教具有等同的地位,這地位好比英國的皇室──也就是某一類生活方式的具體象徵,但對日常生活的運作幾無重要性可言。這不是不好,只是說明了,幾乎看不出誰確實對天主感興趣。我們更感興趣的是對德行、正義、合宜的生活方式,或甚至為敬拜天主、互助及公義之故建立團體。但到最後,倫理哲學、人性本能、不加掩飾的利己之心,才是我們投入這些活動的動機,而不是因為與生活的天主交往所滋生的愛和感恩。天主不僅缺乏市場,就連在我們的宗教活動及宗教熱情中,也往往不見祂的蹤影。 在我們信友中,無信不只是那麼一點點而已。天主代表某種身心症、某種宗教、某種事業……卻極少被看作是一位生活的、啟發的、使人安慰的、具有挑戰性的人物,祂本身使這日常世界相形見絀。 尼采在他《快樂的科學》(The Gay Science)一書中,道出這樣的場景。一個瘋子,在大白天裡,點亮一盞燈,衝進一個擠滿人? 的市場喊叫著:我要找天主!我要找天主!4但是市場裡的群眾都取笑他。「祂走失了嗎?」一人問著。「祂大概像小孩一樣迷路了吧?」另一人問著。「祂躲起來了?還是在怕我們?」他們喊著、譏笑他。然而瘋子轉向他們並喊說,「天主是死了,我告訴你們,是我們殺了祂,你們和我。我們全體都是祂的謀殺者。但是我們怎麼做了這事?我們如何能夠飲盡海水?誰給了我們海綿去拭盡整個地平線?這世界所擁有的一切中,最神聖、最有能力的,卻在我們的刀下流血至死。」然後他沉默不語,把他的燈摔毀在地上,並且宣告說:「我來得太早了。要人們了解這事,仍然還有一大段距離,但他們已經這麼做了。他們殺害了天主!」 人如何能夠殺害天主?尼采在這寓言中所說的,就是「不信」(可說是一種無神論),並非只存在於將自己視為信友的人群之外。它乃是信者群中的一種現象。無神論與無信的問題,不在於否認天主的存在,而在於天主從信友的日常意識和生活中缺席,不夠活躍、不夠重要。就是以這種方式,「我們殺害了祂」。 為何是這樣?為何天主不再活躍於我們日常的生活和意識中?這有兩種解釋。兩種都有人仔細琢磨過。 聖十字若望曾寫道,我們會經驗到天主的沉默,因為天主能是「隱祕的」,或者因為我們是「盲目的」……就像一件物體之所以模糊,是因為它距離太遠,或是因為我們的視力不良5。因此,天主可能撤走祂的臨在,為淨化我們的信德(若望所指的「隱祕」),或者,我們只能微弱地經驗天主,因為我們自身有某些問題(若望所指的「盲目」)。前者他稱之為「靈魂的黑夜」,而後者則是默觀上的錯謬。 近代神學的爭論卻把這種區別兩極化了。保守派與自由派都同意,今日我們對天主的經驗絕非它應有的狀態。這點共識之後他們則漸行漸遠。保守派整體而言,將問題歸因於聖十字架若望所謂的「盲目」:我們生活的方式有某些錯誤,使我們難以企及對天主的經驗。另一方面,自由派則傾向將此情形看作「隱祕」方面的問題。我們對天主的體驗是薄弱的,因為我們正在被淨化,透過靈魂的黑夜,被引領到對天主更成熟的體驗。誰是對的呢? 這兩種狀態乃是同時運作。通常在各個時代,我們的信仰掙扎,不但是因為天主藉撤回祂慰藉的臨在,主動地考驗我們,也是因為我們從未如本來應有的那般忠信。天主始終若隱若現,而我們總是半明半盲。 在此,我的目的不是去爭論我們對天主現有的體驗薄弱,到底是因為天主正引領我們進入更深一層的信仰,還是因為我們自身有某些不對勁。而其實一直是兩樣都有,但我意欲聚焦於後者。我選擇這條路,不是因為我覺得保守派的主張比自由派的更正確,而是因為我對於天主的自由、天主是否選擇給予我們靈魂的黑夜,畢竟是無能為力。然而,我們可以在自身對天主的意向上做些努力。我們的重點會放在信仰上的掙扎,雖然它成了我們自身的過失,但也能夠加以改善。 在我們內不夠完善,使我們對天主的體驗變得遲鈍、模糊的是什麼?若是每一時代有其特殊的不幸,那麼,我們這時代不幸的宗教掙扎根源為何? 體驗天主方面的掙扎,不是天主的存在或不在,而比較是在我們的意識中,天主是否臨在。天主總是臨在,但我們卻不常想到天主。正如一位靈修作家所說,「天主在教堂裡同樣也在酒吧中,但是,一般來說,我們在教堂裡比在酒吧裡更常想起祂」6。 耶穌說:「心地純潔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瑪五8)。意識到天主是一種心智的狀態,就是純潔。經典的靈修作家們通常將心的純潔與默觀相連。透過默觀去淨化意識,以能更好地體驗天主,這樣的掙扎就是尋求更完滿的覺察的掙扎。在今日的西方文化中,我們大部分人只有萎縮的默觀能力、模糊的自我覺察。天主雖臨在我們面前,但我們沒有想到祂。我們缺乏默觀的能力,因此,我們缺乏對天主活躍的體驗。在日常意識中天主的消隱,是默觀上的一個錯謬。這是什麼意思呢? 天主的消隱是默觀上的錯謬 我們的自我覺察怎麼模糊的?我們為何缺乏心靈的純潔? 經驗有質量方面的區別,也有開放程度上的區別。我們的意識和清醒,在程度上有多有少。天主也許強烈地臨在某一事當中,但是我們過於在意、專注於我們的頭痛、心痛、工作、白日夢、令人分心的不安,以至於忽略了那臨在。 這些事情嚴重地限制了我們的覺察。通常,我們真正覺察到的事物遠少於實際所能覺察到的事物。日常經驗的質量與深度大體上決定了我們是否覺察天主。關於天主臨在於何處,我們或是沉睡,或足夠清醒。對日常生活的覺察或無所覺察,則取決於我們默觀的能力。 「若是每一時代有其特殊的不幸,那麼,我們這時代不幸的宗教掙扎根源為何?」 默觀與覺醒有關。所謂默觀,是去完全地體驗一件事,包括它的所有面向。聖經上稱此為與天主、與他人及宇宙「面對面」相遇(格前十三12—13)7。當我們面對現實事物,不因自戀(我們的頭痛及心痛)、實用主義(我們的緊迫工作)以及過度不安(我們的幻夢及分心)所帶來的限制和扭曲影響我們的經驗時,我們就在默觀。 靈修作家們,如聖十字若望,向我們保證,假使我們的覺察未被縮減或扭曲,在日常經驗中應會感受到無窮與神聖,也就是感受到天主。若我們對日常經驗保持完全的清醒,隨之而來的是對天主的一種直觀(contuition)8。但假使我們日常的覺察有所縮減,不是默觀的,那麼天主便在我們的意識中死去,最後連在教堂中亦然。 我們與無信的掙扎,企圖在日常生活更真切地感受到天主,其實是一個與默觀的掙扎。但是我們難道不是天生的默觀者嗎?心理學及社會科學的研究,沒有給我們更深的自我了解嗎?難道我們今日不是更甚於以往,渴求獨處、平安與寧靜嗎? 這一切確是如此。但是這些事情中,沒有一件談到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保持默觀。很明顯地,我們對天主的感覺十分薄弱。這只能意謂著,我們的默觀感覺也同樣薄弱。為何是這樣呢? 我們很容易陷於對當代文化過度悲觀,要不就是絲毫不加批判。按各人的性情,我們要不就樂觀,要不就悲觀,不是自由派,就是保守派,因此,在評估任何情形時,很容易過於慷慨或過度批評。要評價我們的文化,首先應該指出它的矛盾性。我們的文化有它的長處及弱點,而這些弱點往往正是其長處的陰暗面。不過,顯然內在性及默觀不是它的強項。神學家若望.俄格拉弗(Jan Walgrave)曾評論道:「我們的年代共謀了對內在生活實質上的威脅」9。 這當然並非某個團體出於利益而摧毀價值,狡猾而刻意為之的陰謀。但各種歷史因素的偶然匯流,西方歷史中諸多造化弄人,使我們更加難以活出深刻的生活。 哪些影響力謀害著內在生命?現下普遍存在某個簡化的看法,認為今日信仰的掙扎肇因於一九六○年代的社會變遷。此一看法指出,搖滾樂、披頭四、越戰、毒品、性解放、經濟富裕,首次由窮致富世代的出現、新科技,各種旅行與隱埋出身的機會,改變了我們對家庭、婚姻、倫理、天主及宗教的概念。西方世界過去三十年,生活已有根本上的轉變,隨這轉變,舊時關於家庭及宗教的理想都遭受損害。今日有關信仰的諸多問題,依照這一看法,均根植於發生在上一世代的社會變遷。 這看法過於簡化。當尼采筆下的瘋子摔毀他的燈並喊道:「上帝已死,我們是祂的謀殺者!」他所談到的歷程,早已延續好幾世紀。當這世代感覺到天主之死時,他們不過是站在一個長久歷史過程的最後階段,在不知不覺中,逐漸地、一步步地殺害了天主,甚至用著與原本令天主在我們內心活躍相同的方法來殺害祂10。現時的危機,其根源溯及數百年11。 我們的世代與此一實際上的無神論掙扎的理由,根源於西方歷史中文藝復興來臨、現代科學與哲學肇始所帶來的轉變。當時所種下的一粒種子,終在二十世紀後葉開花結果了。 註釋: 1. 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一部第一章。英譯者為Maude。 2. 尼采,《快樂的科學》。英譯者ET. W. Kaufmann,(NewYork: Vintage Books, 1974), p. 167. 3. Philip Rieff, The 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6). 4. 本段中引文均取自註二引用之版本。F.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Book 3, no. 125, p. 182. 5. John of the Cross, The Living Flame of Love. Commentary on Stanza 3, numbers 70-76, translated by K. Kavanaugh and O. Rodriguez. ICS Publications(Wahsington, d. C., 1979), pp. 637-40. 6. Sheila Cassidy, Prayer for Pilgrims(London, 1980), p. 61. 7許多靈修經典作家均採用此一對默觀的定義,如聖十字若望。 8. 「直觀」(contuition)一詞原出自於一位在斯坦布魯克(Stanbrook)修院的本篤修士之作品Medieval Mystical Tradition and John of the Cross(London, 1954), p. 70。法雷爾(Austin Farrer)在他的哲學論文Finite and Infinite: A Philosophical Essay(Westminster,1943)中也使用此詞。法雷爾提到,在「日常感知」(ordinary perception)中,若此感知能力向現實的各個面相開放,人除了「領會」(perceives, or "contuits")到有限之外,也能領會到無限。所以這一詞彙與「直覺」(intuition)一詞意思並不一樣。「直覺」意指人在嚴格意義上的感知及隨之而來的理性推論之外,所捕捉到的事物;「直觀」則指人心所見超越感官的感知能力,但始終「伴隨」著感官的感知,是這感知經驗的一部分,因此,直觀亦屬於日常的感知,也可以說是感知經驗屬於默觀的那一面。 9. 此語本為私人談話,後來發表為短文。見Ronald Rolheiser, "Just Too Busy to Bow Down," in Forgotten among the Lilies(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0), pp. 12-114. 10. 我們常以不好的宗教殺害天主。無神論往往出自於極差的有神論。Michael Buckley在他的大作中有討論,見At the Origins of Modern Atheis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 關於這些歷史根源的分析,可參考Ronald Rolheiser, "The Deeper Causes Underlying Our Present Diffi-culties in Believing, " Louvain Studies(1994).
無試讀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