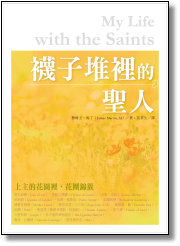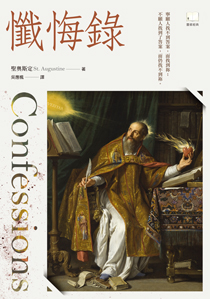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本書目錄
精采書摘
內頁試讀
從孩提時代起,她就是一個「想要得更多」的人。 她聽過福音,但是她沒看到福音落實在生活裡。於是她離開了宗教,尋找另一條路……
孩子看事物是那麼直接、簡單。我看不見任何人脫下上衣施捨窮人,看不見有人設宴款待跛子、聾子和瞎子。那些有在執行這類事情的人,一點也不吸引我,例如當時的「救世軍」。我需要(儘管當時我毫無頭緒),我需要的是一種整合。我要生活,要豐富的生活,我也要別人同樣過著豐富的生活。我不想只為少數貧苦的人表現仁慈,不想像「救世軍」那般的傳教士心態。我渴望所有人都以仁愛對待彼此,渴望每一個家庭都開放給跛子、癱子、瞎子,像舊金山大地震之後,大家互相幫助的方式。只有這樣,人才是真正活著,才真正愛他們的近人。只有這樣才稱作豐盛的生活。可是要怎樣才能得到這種生活呢?我一點頭緒都沒有。
在社會主義風起雲湧的年代,她念了新聞,走上街頭,開始對社會更深刻的觀看和批判,她似乎選擇了社會主義的道路,過著波西米亞的生活,但是她仍然感到不夠滿足……
我曾經在城裏和飯店員工、成衣工人一起罷工,深深體會到罷工者的無力之感,他們因為抗議而被強制驅離。我曾經覺得,為了正義,把自己搞得像唐吉訶德(Don Quixote)對抗風車那般愚蠢,是徒勞無功的。照同類報紙的說法,每一種罷工都是不公義的。報中又提到,每一次罷工都因為無法爭得工人的要求而失敗收場。可惜讀者們從沒有考慮到這些漸進的收穫,這些收穫是經過無數的失敗而從雇主手中榨擠出來的。而那些站在罷工者糾察線上的人,常被認為是錯的一邊,這是我為勞工所受過最大的痛苦。
她孤獨地自問:到底有沒有一條不一樣的路,讓人能活得更像個人?有沒有一個社會,讓人可以更易於行善?
孩子出生了,我的喜樂是那樣大,大到我連在醫院的床上都仍興奮地寫了一篇敘述這新生兒的文章,刊登在《新群眾》(New Masses)。我要向全世界分享我的喜樂!同時,我也很高與能為這份工人雜誌撰寫了這份喜樂,這份所有的婦女都能夠了解的喜悅……儘管她們不斷地因為貧乏、失業和階級鬥爭而愁苦哀傷。
愛情的滿足、生子的喜樂,帶領她歸向愛的源頭,也帶領她走上她一直在尋求的更深、更廣的道路,所有曾經走過的路,都沒有浪費……
桃樂斯‧戴(Dorothy Day),為社會運動創造出一條非凡道路。
相關推薦書籍
作者相關書籍
目次 導言 ──詹姆士‧馬丁(James Martin, SJ.) 告解
第一部 追尋 先祖 天主又是什麼? 第三十七街 家 青春期 大學時期 東部 新聞工作 ?眾 監獄 自由作家 帝王郡 在追尋中的歲月
第二部 幸福的溫度 人為快樂而生 有了孩子 愛心滿溢 工作與旅程
第三部 愛的量尺 低下階層的農夫 報紙、人與工作 勞工 團體 家庭 「戰爭使國家健康」 彼得之死 基利斯堤街 後記
導言
詹姆士‧馬丁(James Martin, S.J.)
西元一八九七年,桃樂斯.戴誕生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Brooklyn)內一個聖公會(Episcopal)的家庭。幼年時,舉家搬遷芝加哥(Chicago)。父親是新聞從業人員,經常需要找一份好工作。她在就讀伊利諾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時,立志寫作的生涯,同時也關懷當時激烈的政治議題,諸如,貧窮、急遽的社會變遷、勞工組織等,不過,顯然地對宗教沒什麼興趣。透析事理、精密立論是她寫作的特色(也是她的思想上的特色)。在她這本自傳《漫長的孤寂》中,回顧了這個時期的她:「當時,我認為宗教只會妨礙我的工作。我覺得,它真的是人民的鴉片,所以,我硬下心腸,不去管它。那是一個自己知道而且故意的過程。」
大學沒有畢業,她就前往紐約,去從事記者的職業生涯。一頭栽進紐約市內格林威治村那種波希米亞式的世界,為激進的社運小報《呼喚》(The Call)和《群眾》(The Masses)撰稿,採訪相關的議題,諸如,社會主義運動、工人至上主義、國際工人聯盟、「飢餓暴動」、失業、市政廳前的抗議遊行、童工法案等。「我在紐約市見過托洛斯基(Trotsky,譯按:蘇聯共產革命早期的領導人之一),那時他還未回去蘇聯。」她這樣記載著。在首都華盛頓的一次爭取婦女投票權的遊行中,她被捕下獄。
這個短暫的牢獄禁錮,反倒沉澱出了一個歷久而不衰的思維。在此拘留期間,她目睹受監人犯所受的不人道待遇,而和一起被下獄的婦運同志,共同發起了一項在獄中的絕食抗議行動。此舉深化了她認同社會上為數更多的一群弱勢者:貧窮者與被剝削者。在本書中,她回顧了在這段監禁期內的反思,她自身的過犯型態,和那個廣大世界中人們的受苦受難以及邪惡,是脫不了關係的,依照
依納爵神操的用詞語句,桃樂斯是正處在《神操》的第一週的默想。
三十天以後將重獲自由,這對我將毫無意義可言。我將再不會有自由了。不能自由,是因為得知,對於全世界所有禁錮在鐵窗後的男、女、老、少,固然他們因犯罪而被監禁、受懲處、孤獨和受苦,然而,對於這些人所犯的這些罪,我們大家都有責任 ……
難道這是過分地誇張了?沒有多少人像我們(譯按:獄中絕食抗議者)這般,整整的六天六夜,平躺在陰冷、黑暗和飢餓中,而內心卻仍然澎湃著這個世界以及我等乃是其中一部分的思緒。
桃樂斯的聰明才智,以及她益發地關懷社會正義,把她帶進紐約市一群活躍的知識分子和社運人士的圈子中。這群人包括愛瑪.戈曼(Emma Goldman),若望.巴索斯(John Dos Passos),麥克.伊斯曼(Max Eastman)、若望.雷德(John Reed)和尤金.歐尼爾(Eugene O'Nell)。也是在這段時期內,她和一個名叫福斯特.貝特漢(Forster Batterham)的男子發生戀情,進而成為有實而沒有名分的夫妻,住在紐約市史坦頓島(Staten Island)一幢老舊的房子中。
西元一九二六年她懷孕了,這件事很自然地導引她產生一個宗教的皈依。懷孕喚起了她的覺醒:對於創造的領悟,以及要與天主發展出關係的渴望。此時,以生活上的各個層面來說,均非順遂。幾年前認識而同居的這個男子,是她在市內的一所醫院工作時認識的。曾經懷孕後不久,又流產了。關於這段情節,她很少公開地談論,只在私下和少數好友曾談到(她有一本小說《第十一個貞女》
The Eleventh Virgin,書中女主角流產一事,似乎是一個影射)。歷經為時數年的戀情、酗酒的一段時光,短暫的放蕩形骸(曾夜宿某一廉價的旅館,被誤認為流鶯而遭逮捕)之後,桃樂斯幡然覺醒,視自己是一名被寬恕的悔過者。再度懷孕幫助她感受到天主給她的寬恕,祂清洗了她的過犯,她的生命得以重新開始。在這滿心感謝的沃土中,信德的種子發芽了。
「我每天祈禱,連我自己都嚇了一跳,是如何開始的。」她這麼寫道。在懷孕期間,她取出了多年前收藏的《師主篇》(Imitation of Christ ,中文版由光啟文化印行),開始捧讀。
該書是根據十五世紀的一個手抄本譯的,在教會內流傳已久,供信友們熱心敬主之用。一位傳記作者特別指出:桃樂斯從年輕時代開始收集了不少書籍,在她日後的生命上大大地派上了用場,諸如,《聖詠集》(The Psalms),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托爾斯泰(Tolstoy)、狄更斯(Dickens)、詹姆斯(James)等名家的著作。根據保祿.艾禮(Paul Elie)在他的《拯救自己》(The Life You Save May Be Your Own)書中是這樣描述的:「閱讀了《師主篇》之後,她未來生命的取向已然明確
── 在宗教領域戮力。」在此過程中,她也決定要讓她即將出生的嬰兒受洗。
在她史坦頓島的住家附近,有一位仁愛修女會的亞羅西亞修女(Sr. Aloysia)主持一所「未婚媽媽之家」。修女的簡樸生活方式,令她心儀。有一天,亞羅西亞修女單刀直入地問她:「如果你自己不先成為一名天主教徒,將來你如何能教養妳的小孩成為天主教徒?」話說得有理,在女兒塔瑪.德蘭(Tamar Teresa)出生領洗後,她也加入了天主教會。
雖然桃樂斯.戴從小就未和天主教會有過接觸,然而,以她一貫的生活態度和對理念的執著追尋來說,天主教會為她是一個理所當然的歸宿。她在奮力不懈地追尋諸多「理念」的同時,也尋找一個系統化的倫理法則,用以支撐這些社會所需的回應,甚至於英勇的行動。曾和她一起打拚的激進派友人的圈子內,是有一種彼此照顧的「團體之愛」和「兄弟手足之情」,但是,在背後支撐的哲學基礎,欠缺如同天主教的教義那樣,有前後一貫、放諸四海皆準的道德體系。
引領她走進天主教的大門,還有另一個理由:天主教會對於貧窮者和外來移民者的認同感,實在令她窩心。在那段格林威治村的日子裏,她常走進附近的一個天主教堂聖若瑟堂(St. Joseph's Church),在那兒不僅有她鍾愛的貧窮者,更瀰漫著祈禱的氛圍。最後,她選擇的是一條對天主謙遜和服從的道路,完全是天主教傳統的神修方式,如邁向至聖之路。桃樂斯對貧窮者的關愛、與天主共融的渴望、道德體系的追尋、希望度著謙遜與服從的生活,全都緊密地結合在天主教會中。
天主教會滿足了她的人生理想和與主契合的新生命,如同多默.牟敦(Thomas Merton)的情況一樣,因為這個龐大而神祕的教會,充滿自信,明確認識在此塵世中的定位。
福斯特這位男士則完全不同,他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對任何有組織的機構,包括有組織的宗教,全無興趣。「無法跟他談論宗教的事,一道高牆已然隔開了我倆。」她悲傷地寫道。女兒塔瑪受洗當天,是彼此關係的緊張時刻。儀式一結束,他就離開,出海去捕捉龍蝦。晚餐時,又是一場爭執。一年後,兩人終於分手。為了皈依天主教,她付出了一個大代價。
桃樂斯擁抱天主教會之後的種種,並非一帆風順、事事順遂。天主教會是貧窮者的樂園,是不錯的,但是,它對於造成貧窮的根源或制度上的原因,似乎視若無睹。她一直在思索、質問著:難道共產主義者是僅有的、願意去幫助貧窮者的人嗎?在私下裏,她不停地思索著,可有一條途徑能把社會正義和她新認識的天主教結合在一起。
西元一九三二年,答案終於出現了。她遇見一位來自法國的彼得.莫瑞(Peter Maurin),因而碰撞出了一個智慧的火花。莫瑞自稱是法國的農夫,上過學,是一所修士辦的學校。桃樂斯鍾意與他來往、請益,「他是一個可以整天和你講個不停的人」,而他的世界觀是世上的人們並非工業化機器運轉的奴隸,而是能夠共同參與美好生命的創造。她在這一本自傳中描寫這個人:
莫瑞很樂意看到人們做出一番偉大的事情,和構思偉大的夢想。他要人們伸出雙手,擁抱自己的弟兄們,因為他知道,找到天主、找到至善境界最穩當的途徑,就是經由自己的弟兄們。他希望這番的努力,終究能達到更佳的物質生活條件,以滿足人們的需求,進而有能力,以各種的方式去愛和敬拜天主。
而這個烏托邦式的視野,其基礎在於聖經的福音。因此,莫瑞的這番認知,深深地擄獲了桃樂斯.戴,而經常讚譽他是她的導師。彼得.莫瑞鼓勵她,發揮新聞方面的才幹,去創辦一份報紙,以便把工人們團結在它的旗下,並能從福音的視野,對悲慘的社會現狀提出批判、指點迷津。西元一九三三年的國際勞工日(五月一日,也是工人的主保聖若瑟的瞻禮日)《天主教工人報》(Catholic Worker)創刊了。
每份報紙售價一美分(至今仍是)。發行首日,全美共售出兩萬五千份。到本年底為止,發行量已達每日十萬份。
報紙發行後,桃樂斯和莫瑞又在紐約市為貧窮者開辦了「待客之家」(Houses of hospitality)。這些中心,在經濟大蕭條期間,為成千的窮困者提供免費的食物和住宿。接著,他們又為貧窮者開辦一種社區型的「合作農場」。「如此眾多的陌生人體生活在一起,多麼罕見!」她在自傳中如此描述。雖然,日後的事實證明,「合作農場」的理念實踐,難以在別的地方複製,但「待客之家」則有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全美遍地生根,後來,更運作成為效果卓著的「天主教工人聯盟運動」(Catholic Worker Movement)。
數十年來,她都以自家住所為辦公室,有一群經常性的志工,一起工作著。她在各地「天主教工人之家」(Catholic Worker house,譯按:由上述的「待客之家」轉型)和在紐約上州(Upstate New York)的「合作農場」的工作與生活型態迥異,但都興致盎然。她廣泛地旅行、視察全美各據點。她是一名新聞從業人,撰寫文章、編輯報紙,同時,在她的眾多跟隨者面前,經由她的臨在和祈禱,以身作則作他們的榜樣。
在各地的天主教工人之家服務的志工們,每天的例行工作是忙碌的。清晨起床後,就要開始準備免費供應的午餐,屆時,將擁入成群貧窮的男女,志工們在供餐服務之餘,還要和他們話家常。下午,清洗碗盤後,各自辦公──跑郵局、付清帳款、整理帳冊、清掃屋內,還要外出設法募得食物。黃昏時,晚禱時間和晚餐服務,大批的人群將在門口排隊,又會是一陣的忙亂。晚間,終能鎖上大門。每週五的晚上,是公共論壇時間,歡迎各界人士自由參加。某些具有條件的中心,還有每日的彌撒,以服務大眾。
跟隨桃樂斯.戴、多年從事義工服務者當中,羅勃.埃斯柏格值得在此一提。他曾著有《諸聖傳》一書。各地的青年志工群,有許多人是大學生,埃斯柏格就是其中之一。在一九七○年代,他從波士頓的哈佛大學休學,以五年的時間,在紐約市的「天主教工人之家」服務,因而對桃樂斯的言行舉止知之甚深。我曾問他,和桃樂斯一起工作的感想如何,「很有趣啊」,這個回答嚇了我一跳。我讀過許多有關她的傳記和報導,但始終無法確定她的人格特質。在印象中,她是個有祈禱氣氛的人,樂善好施、辛勤工作,但似乎性情冷峻,是個抑鬱型的人物,尤其是自傳的封面照片也傳遞這樣的訊息。
「桃樂斯是個風趣的人,她善於說故事,常告訴我們一些她自己的趣事。」埃斯柏格這樣形容她。我記得法國小說家利昂.布洛(Leon Bloy)有一個說法:喜悅乃是聖神一個明確的記號。各式各樣的人們,從工人之家的年輕志工到鄰近社區內年長的流浪者,她都能和他們喜樂地相處自如,不是表面功夫的敷衍,而是真誠以待,能欣賞各人不同的才華、秉賦。然而,她也是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遇到生活上的難題,偶爾也不免灰心洩氣,甚而動怒。還有,依照埃斯柏格的說法,她不喜歡人家「崇拜」她,也不讓別人有機會以傳奇人物來對待她。
總之,她待人熱情易於親近。埃斯柏格很愉快地回憶道:「她是真誠地對待我。」她喜歡什麼?「噢,桃樂斯喜歡閱讀,而且興趣廣泛,從古典小說到偵探小說,無不可讀。偶爾也看看電視。」那她看什麼節目呢?「經典劇場。」我聽了後不禁笑了出來,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一位聖賢會喜歡看電視節目。
終其一生,桃樂斯.戴出於自願地度著一個貧窮、儉樸的生活。穿著的是別人捐獻給天主教工人之家的衣服,出門旅行搭乘巴士等大眾交通工具,而個人的需用品,則盡量地少量。這是一種有尊嚴和自由的貧窮,出於自我的抉擇;這和在貧困的枷鎖下,被奴役的窮苦大眾的貧窮,是不一樣的。後者,非出於自願,而是在不公義和壓迫之下的一種狀態,是需要加以矯正的、制度性罪過的記號。
由於對福音訓誨的一貫了解,桃樂斯鼓吹和平,不遺餘力。「山中聖訓」的訊息,導引她對於採行非暴力手段(Nonviolence),有著不可動搖的承諾。她這種非暴力的心態和從事不合作主義(Civil disobedience)的意願,淵源於二戰
結束後不久的時期(譯按:譬如,印度的甘地在爭取獨立時的運動),一直延續到冷戰和美國的越戰時期。
鼓吹和平行動的結果,是她遭人槍傷、被政府逮捕下獄和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跟蹤與調查。這些都不能阻擋住她,「僕人是不能大於他的主人」(瑪十24),是她經常引用的話。批評的聲浪,也來自教會內曾最支持她的人們。雖說,他們極力稱揚她那為貧窮者的工作和努力,卻發現這種和平主義是一顆難以吞嚥的苦藥,尤其,正當美國的對外戰爭如火如荼的進行之時。這也未能動搖她。在進入一九六○年代,美國社會公開的抗議活動愈來愈普遍時,桃樂斯.戴以言以行的見證,已然是新世代鼓吹社會正義的標竿。
七十六歲那一年(西元一九七三年),她參加了「農場工人聯合會」(United Farm Workers)為支持西撒.查維茲(Cesar Chavez)和外籍勞工的權益,而舉辦的一個盛大的集會,因而被捕下獄。當場拍攝的一幀黑白照片,震撼人心──一位嬌小瘦弱的灰髮老婦人,身著二手的老舊洋裝,坐在一張折疊椅上,昂首凝視在她身前聳立的兩名魁梧高大的武裝警察。它刻畫出,一輩子的一個承諾、基督徒的尊嚴和福音訓誨的絕對正確性。
《漫長的孤寂》於一九五二年出版。最近她的日記《喜樂的義務》(The Duty of Delight)才剛出版,向世界透露出她的新面貌。我在此簡述一些枝節,讓讀者更能了解本書對她一生的描述。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紐約天主教工人之家中出入的人,往往是些有缺陷、心智情緒不穩定、易憤怒的人,因此在她的日記中不時會描述一些當時會遇到的威脅、憤怒、恐嚇等暴力情形。此外,在任何組織中,總會有些爭論,這一切都不斷磨損她的精力。她在一九三五年的日記中,記錄了令人難忘的一則:「如果你失望、沮喪,人們會因此再度陷入失望甚至憤怒;如果你不氣餒,大家便會使你氣餒,而且會因為你的不氣餒而生氣。」這是每一個修會的創辦人或是任何偉大行動的推行人都會遇到的相似情況。
在這新出版的日記中,也可以看到她不斷追尋聖善的痕跡。她常常省察良心,對基督的教訓全心信奉。她時常譴責自己無耐性或尖刻地批評他人。但這些日記並不是病態的,而是充滿希望:她看到自己在踏上走向天主的路,並且永遠處於聖寵的恩賜中。一九七五年,她七十八歲,她察覺到自己抱怨太多,因此寫道:「在生活中,我需要更平靜,我必須減緩,別人要增強……什麼時候我才能學會?」
今天,桃樂斯.戴給人的印象之一是她把女兒託付給別人照顧,而自己卻專注於「天主教工人運動」。(在這本自傳中,她的確不知不覺地給人這種印象,因為她花太多時間談及天主教工人運動,很少談到她的女兒。)
其實這是個假象,因為在她的日記,收錄了一大堆關於她回維蒙特州(Vermont)望女兒及孫兒們的紀錄,其中充滿愉悅的家庭氣氛。例如,她寫道:「我們早醒來,路上結滿了冰,學校停課,所有孩子都留在家裏。」一九五九年她又寫道:「艾力克(Eric)滑了好幾次雪撬,史丹利(Stanley)和大偉(David)在木材……甚至十七個月大的希拉利( Hilaire)在他們把木柴搬進地窖時,也要幫一手。」她就像所有的祖母一樣描述她的家庭生活。這些描述有助於讀者了解《漫長的孤寂》。
幾個月後,桃樂斯.戴接到與福斯特同居的女人南內特(Nanette)的訊息。得了癌症,請求桃樂斯.戴看顧她。桃樂斯.戴答應了,但從沒有公開寫及這。她照顧南內特直到她生命終結之日,並不時給心煩意亂的福斯特打氣。這是英勇的仁愛工作。她寫述到南內特時說:「她絕望的嘆息真叫人心痛,而福斯特時常不在,他想失去知覺,好能逃避一切。」南內特死前要求領洗。
她的日記也透露她最令人難忘的行動:主持天主教工人運動的事務、按月撰專欄《朝聖之旅》(On Pilgrimage)、為和平抗議、求若渴地閱讀,並周遊全國各地作演講。大公會議期間她曾兩次到羅馬,其中一次她寫給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一封信,請求他強力譴責戰爭。長久以來,她努力做批評家羅斯金(John Ruskin)愛說的:「喜樂的義務。」她常在公開場合中談到這個主題。一九六一年她寫道:「我在想,一個人年紀愈大愈容易悲傷,我們如何知道此世是十字架的苦楚,而又要如何每天盡力去戰勝它,在愛中成長,著愛而得到喜樂。」
桃樂斯.戴的一生表現出許多價值:實行福音的教訓,與窮人生活在一起、以非暴力作為推動和平的方式,以及在教會中團結的重要。她又支持那自以為滿罪惡、不能有所作為的人。她過去因隨興的性關係而煩惱,她曾墮胎,她與福斯特的關係混亂,許多過去迷糊的經驗,促使她去追尋生命更深的意義。這一切乎也使她接受了一個賞賜 —— 一個嬰孩,並以更大的感激去接受她的聖召。
她可以說是隱修士多默‧牟敦的寫照。牟敦年輕時也因為有過一個小孩,使他開始尋找他在聖寵中的身分。有時候,最偉大的聖者即是那走在最崎嶇道路上的人。這一切是我從《漫長的孤寂》中學到的。
許多年前,我在一個堂區帶避靜,桃樂斯.戴的一生給我許多啟發。在紐約市北部一間簡陋的避靜院,我的講題是「與諸聖同禱」。
談到最喜愛的聖人時,另一位避靜指導員、一位女士及母親,娓娓地談起她心目中的英雄──桃樂斯.戴──的一生。
結束時,她談到桃樂斯.戴的過去,她說:「想想看,假使桃樂斯.戴當初自己說:『我墮過胎,我還能做什麼?』假使她這麼想,那後來一切美好的事都不會發生了。」
詹姆士‧馬丁,耶穌會士,著有《襪子堆裏的聖人》(My Life with the Saints)等書(光啟文化事業出版,民國九十八年
,范京生譯),其中有一章即是關於桃樂斯‧戴,此導言部分摘錄自該書。
無試讀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