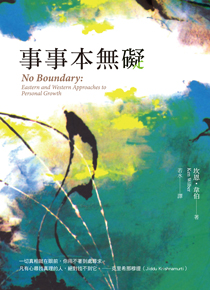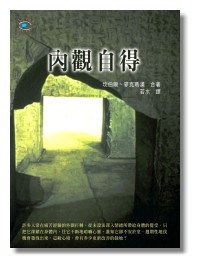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本書目錄
精采書摘
內頁試讀
生命並不是模稜兩可的玩意兒,而是非常真切具體的東西,正如人生的使命也非常真切具體一樣。這些使命,構成了人的命運;每個人的命運都獨一無二且各有不同,無法同別人互作比較。
本書簡介
創作「意義治療法」聞名於世的弗蘭克(Viktor E. Frankl)是一位精神官能學及精神分析學教授,對心理學界的影響及貢獻至深且鉅。納粹當政期間,曾被囚於集中營內,忍受種種非人待遇而終獲生還,因而對存在的痛苦、挫折,及現代人特有的焦慮與空虛感,特別關注。其見解深銳而透徹,為心理學注入前輩諸大師所疏忽的人道精神,開創了心理學的新里程。
本書以作者的集中營經歷為本,揭示人類生命的動力在於尋出意義;人只要參透為何而活,即能承受任何煎熬;而無論處境如何,亦皆有自由抉擇的餘地。本書深入淺出,但振聾發聵人人可讀。
自出版迄今,轟動全球,堪稱為研究人類心理學與精神不可不讀的一本經典之作。
相關推薦書籍
新譯本序 趙可式/009
代序 戈登歐伯/013
第一部 集中營歷劫/019
一場硬仗
掙扎生存時的道德問題
鼓足勇氣,現身說法
苦役的代價
入營第一關
由驚駭到視若無睹
冷漠是自衛的妙招
精神創傷
非人的境遇
比噩夢還恐怖
畫餅充飢
「性」趣缺缺
宗教熱
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死囚的美感經驗
營中藝術活動
集中營幽默
苦中作樂
救命仙丹
獨處的渴望
人命如螻蟻
德黑蘭的死神
自由的曙光
吃癟與吃香
臨時舍監
抉擇與自由
超越當前的困境
精神防線
參透「為何」,迎接「任何」
尋出生命的意義
集體精神治療
天使和惡魔
獲釋後的營俘心理
人格解體
宣洩
重獲新生
精神失調的危機
直如一場噩夢
第二部 意義治療法的基本概念/119
求意義的意志
存在的挫折
心靈性精神官能症
心靈動力學
存在的空虛
生命的意義
存在的本質
愛的意義
苦難的意義
形而上的臨床問題
演劇意義治療
超越的意義
生命的短暫性
意義治療是一種技術
集體性精神官能症
泛決定論的批判
精神醫學的信條
再賦予人性的精神醫學
註釋/162
弗蘭克重要著作目錄/174
第一部 集中營歷劫
一場硬仗
本書並不以集中營實錄自詡。書中所載,只是數百萬集中營俘虜反覆身受的痛苦經驗。這是一個集中營的內在故事,由一位生還者所述。書中沒有那屢經描繪,其實不太有人相信的大恐怖;有的只是多如牛毛、層出不窮的小折磨。換言之,本書只想為這個問題尋找答案:「一個普通的俘虜每天生活在集中營裡,會有怎樣的感觸?」
本書所描述的事件,大都不是發生在著名的大型集中營裡,而是發生在屢見殘殺的小集中營裡。書中故事,不是英雄烈士的苦難事蹟,也不是酷霸(Capos,囚犯中擔任監管之職,且擁有特權者)或知名俘虜的生活點滴。它所關切的,不是有權勢、有地位的人所受的苦,而是諸多沒沒無聞、名不見經傳的俘虜所遭遇的苦刑、苛虐,及死亡。眾酷霸真正瞧不起的,正是這些平凡無奇、袖子上一無標記的俘虜。他們幾乎無以果腹,而酷霸卻從不知飢餓為何物。事實上,許多酷霸在營期間的膳食,比這輩子的其他時候還要享受。但他們對俘虜的態度,比警衛還要刻薄;打起人來,也比納粹挺進隊員還要狠。當然,酷霸是由眾多囚犯中精挑細選而來的。他們的個性,恰恰適合擔任這種酷虐的角色;如果「工作」不力,有負所託,立刻就會被刷下來。因此,他們一個個都賣力表現,儼若納粹挺進隊員和營中警衛。像這種例子,也可以用同樣的心理學觀點來衡量。
局外人對集中營生活,很容易抱著一種帶有憐憫與感傷的錯誤觀念,至於對營中俘虜為圖生存而奮力掙扎的艱辛,則不甚了了。這種掙扎,正是為了日常口糧、為了生命本身,為了自己或好友而不得不全力以赴的一場硬仗。
掙扎生存時的道德問題
且以換營為例。換營消息,是由官方發布的,表面上說是要把一批俘虜轉運到另一個營區。然而你如果料想這所謂的「另一個營區」其實就是指煤氣間,你的推測可以說八九不離十。病弱而無力工作的俘虜,都會遭到淘汰,並且遣送到設有煤氣間和火葬場的大型集中營裡。淘汰的方法,是教全體俘虜來一場群毆,或者分隊格鬥。當其時,每個俘虜心中最記掛的便是:努力把自己和好友的
名字,排除於黑名單之外──儘管大家知道拯救某人,有可能會被發現。
每次換營,總有一定數量的俘虜非走不可。然而,由於每個俘虜不過是個號碼,所以究竟走了哪些人並沒多大關係。俘虜在入營之時,隨身證件和其他物品就已經遭到沒收了(至少奧殊維茲集中營Auschwitz是這樣做的),因此,每個人都有機會虛報姓名職業。許多人為了各種理由,就都這麼做。當局所關注的,只是俘虜的號碼。這個號碼,就刺在各人的皮膚上,也繡在衣褲的某個地方。任何警衛若想「整」一個俘虜,只要對該俘虜的號碼「瞟」一眼就行了(這一「瞟」,即可教我們心驚肉跳),根本不必查問姓名。
言歸正傳,換營隊伍行將離去時,營中俘虜是既不願也沒有時間去顧慮道德或倫理問題的。每個人心中只有一念,那就是:為等候他回去的家人而活下去,並且設法營救朋友。所以,他會毫不猶豫地想盡辦法弄到另一個人,另一個「號碼」,來代替他加入換營行列。
我曾提過,挑選酷霸的方法十分消極,只有最殘暴的俘虜才會被挑出來擔任這個差事(雖然也有些僥倖的例外)。不過,除了由挺進隊負責挑選之外,還有一種毛遂自薦的辦法是在全體俘虜之間全天候進行的。一般說來,只有經過多年輾轉遷徙,為掙扎生存已毫無顧忌,並且能夠不擇手段、或偷或搶,甚至出賣朋友以自保的俘虜,才有可能活下來。我們這些仗著許多機運或奇蹟──隨你怎麼稱呼──而活過來的人,都知道我們當中真正的精英,都沒有回來。
鼓足勇氣,現身說法
有關集中營的報導和實錄,多已有案可稽。可是,事實真相,只有附屬於一個人的經驗時才有其深意。本節所要描述的,正是這些經驗的特質。筆者願意以當今人類所擁有的知識,為曾陷身集中營的人闡釋當時的經驗,並幫助未曾身歷其境的人理解、體會這極少數浩劫餘生、如今卻萬難適應正常生活的人所曾身受的歷練。這些歷劫歸來的生還者常說:「我們不喜歡談過去的經驗。身歷其境的人,不必別人多費唇舌來替他解說;沒有經驗過的人,不會了解我們當時和現在的感受。」
要有條不紊地闡述這個主題,實在相當困難。畢竟,心理學家總該維持其學術上的超然。可是,一個坐囚期間從事其研究觀察的人,是否擁有這必要的超然呢?局外人必定有這種超然,可是往往因為相距太遠,事不關己,而無法作出真正有價值的論述。這種事,只有局內人最清楚。他的判斷容或不夠客觀、不夠公允,但這原是無可避免的。如果他想要避免任何個人的偏見,就必須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這也便是撰寫這樣的一本書的困難所在。有時,作者必須鼓足勇氣,寫出極其隱私的經驗。我在撰寫當時,就曾經打算隱匿真實姓名,只附上我坐囚期間的俘虜編號。可是脫稿之時,我又發覺如果匿名出版,本書的價值勢必減半,更何況我必須有勇氣公開陳述我的信念。因此,我儘管十分不願暴白自己,卻沒有刪去任何章節。
把本書內容濃縮成理論的工作,我將留待他人去做。這些理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深受矚目,而其「鐵絲網恐懼症」為眾所知的監獄生活心理學,可能有所貢獻。最近,人類在「大眾精神病理學」(容我引用LeBon的一本著作中的著名詞句及書名)上的進展,可以說拜第二次世界大戰之賜,因為這場大戰製造了神經戰和集中營。
苦役的代價
本書所述,乃是我在集中營中身為一名普通俘虜的經驗。因而,我特別要聲明的是,被俘期間,我除了最後幾個星期之外,並未受僱擔任營中的精神病醫生,甚或是一般科的醫生。我提到這一點,難免有些自豪。我有幾個同行相當幸運,能夠在簡陋且僅供應繃帶(由破布和廢紙作成)的急救站工作。我的俘虜編號是一一九、一○四,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鐵路沿線上挖土和鋪鐵軌。有一次,我獨力挖掘一條地下水管的通道。這項功績後來得到了報酬。就在一九四四年聖誕節,我收到一份所謂「獎金聯券」的禮物,是由承包該項工程的建設公司發給的。我們這些俘虜,實際上是被集中營當局賣給這家公司當奴役,該公司每天按俘虜人數付給當局一筆固定的工資。每份聯券約值五十個芬尼克(為德國小銅幣,值百分之一馬克),可以兌換六根香菸。兌換時間,通常在幾星期後,不過有時候也會失效。於是乎,我成了個驕傲的「財主」,擁有一份值十二根香菸的禮券。這十二根香菸本身或許無甚意義,卻可以兌換十二份肉湯,而十二份肉湯在當時看來,委實是一道消飢救急的大餐。
抽菸的特權,只保留給每星期都有固定獎券配額的酷霸,和在倉庫、工作場所擔任守衛,或領取幾支菸作為擔當危險職務酬勞的人。除此之外,就只有已喪失生存意志,想「享受」生平最後幾天的俘虜,還可以擁有這個特權。因此,我們一旦看到一個同伴在抽菸,就知道他已經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和信心;而生存意志一旦喪失,便很難以恢復過來。
入營第一關
現有大批資料,為眾多俘虜的經驗與觀察的結晶。當我們仔細審視這些資料,將會發覺眾俘虜對集中營生活的心理反應,可分為三個階段:入營之後的階段、囚於集中營例行生活的階段、釋放且重獲自由之後的階段。
第一階段最顯著的徵狀便是震驚。在某些情況下,俘虜也可能在正式入營之前即已有此徵狀。
且以我個人入營時的情況為例。當時,共有一千五百人在火車上度過了幾天幾夜,每節車廂有八十個人,每個人都得躺在自己的行李(即個人僅餘的身外物)上。車廂內因為擁擠不堪,鴿灰色的晨曦只能由車窗頂端透進來。每個人都以為火車會駛向某個軍需工廠,然後大家會在那兒充當強制勞工。沒有人知道我們是否仍在西里西亞(Silisia,位於歐洲中部),或者已經抵達波蘭。火車的汽笛聲一如求救的呼喊,聽來十分淒厲,像是要為一步步挨近地獄的可憐乘客叫冤抱屈似地。不久,火車轉轍了,顯然已接近一個大站。突然間,一廂廂憂心忡忡的乘客紛紛驚叫:「那兒有個牌子,奧殊維茲!」霎時,每個人的血液都降到冰點。「奧殊維茲」是恐怖的代名詞,代表著煤氣間、火葬場、大屠殺。火車慢慢地、近乎遲疑地行駛著,彷彿希望為乘客拖延真相大白的一刻:奧殊維茲!
晨曦漸露,一座龐大的集中營逐漸現出輪廓。幾排長長的帶鐵絲網籬笆,幾座守望塔、探照燈,以及一列列憔悴襤褸的人形沿著荒涼的石路蹣跚走著,在灰白的晨曦中,不知要邁向何處。有幾聲零落的吆喝和指揮的哨聲,卻不知有何含意。想像中,我彷彿還看到有幾座絞刑臺,上面吊著晃來晃去的死人。我不覺毛骨悚然,然而這還不算什麼,因為隨後一個遙無止期的大恐怖,正等著我們去適應哩!
火車終於到站了。一聲聲吆喝,打破了起初的靜默。此後,我們在所有的集中營裡,就一再聽到這粗魯而尖銳的噪音。它酷似罹
難者臨死的哀嚎,所不同的是,它帶著刺耳的沙啞聲,彷彿發自一個不得不常如此叫嚷,或一再遭受謀害的人的喉間。車廂門立刻被推開了,一小隊著條紋制服、剃光頭,看來營養不錯的俘虜衝將進來。他們操著各種歐洲語言,而且全都帶有一些幽默;只是此情此景,這種幽默聽來未免怪異。就像垂死掙扎一樣,我骨子裡的樂觀(這種樂觀使我每逢最險惡的境地也常常能克制自己)緊緊攫住這個念頭:這些俘虜氣色不錯,精神似乎很好,甚至還笑得出來。說不定,日後我也可以掙到他們今天這種地位呢!
在精神病學裡,有一種病叫做「緩刑錯覺」。死刑犯在處決以前,幻想自己會在最後一分鐘獲得緩刑。同樣地,我們也抱著一線希望,直捱到最後一刻都還相信結果不會這麼糟糕。先看到那些俘虜的圓臉和紅潤的雙頰,就已經是一大鼓勵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這批俘虜是經過特選的中堅分子,多年來一直負責接收每天湧入車站的乘客。而所謂「接收」,包括點數新到的俘虜、搜查隨身攜帶的行囊,其中凡是稀有物品或走私來的珠黃,一律沒收。在大戰的最後幾年,奧殊維茲在歐洲想必是一個奇特的地方。珍貴的金銀財寶,必定不只鎖在碩大的儲倉內,還掌握在挺進隊員手中。
一千五百名俘虜,都被關進一間頂多只能容納兩百人的庫房裡。我們飢寒交迫,庫房內連蹲的地方都不夠,更別說躺下來了。四天之中,我們僅靠一片五盎斯重的麵包果腹。然而,我卻聽到幾個看管庫房的資深俘虜用一枚白金鑽石領夾和一名負責接收的俘虜談交易。大多數的利潤,最後都用來買醉──這兒可以買到杜松子酒。足夠一夕酣夢的杜松子酒,究竟需要花幾千馬克才能買到,我已不復記憶;可是,我卻知道那些長期受到監禁的俘虜需要杜松子酒。在這種情況下,誰能責怪他們花錢買醉、麻痺自己呢?還有一批俘虜也有酒可喝,並且由納粹挺進隊無限制供應。這些俘虜都在煤氣間和火葬場工作,他們深知終有一天,自己會被另一批人取代,也深知自己終究會由目前這不得不幹的劊子手角色淪而為罹難人。
我們這一梯次的每個人,差不多都有個癡想:料想自己可以逢凶化吉、消災解厄。火車到站時,我們還不確定下一步的命運,有人教我們把行囊留在車上,然後分男女排成兩行,以便逐次由一名挺進隊的資深長官面前通過。教人吃驚的是,當時我竟膽敢把我的背袋藏在外套裡邊。我這一隊繼續前進,一個個從這位長官面前經過。我很清楚,這官員一旦發現我暗藏背袋,必定教我吃足苦頭;根據過去的經驗,我知道他至少會狠踢我一腳。我本能地挺直腰桿走向這位長官,免得他瞧出我身上的重物。不久,我與他正面相對。他身材高,合身的制服纖塵不染;反觀我們,漫長的旅途之後,已經是蓬頭垢面、一身邋遢,跟他呈強烈的對比。他擺出一副漫不在乎、悠然自得的姿態,左手托著右肘,右手直立,並用右手食指悠閒地指向左,或指向右。我們絲毫不知道這傢伙的手指頭一忽兒指向左,一忽兒指向右,究竟有何不祥的含意。只是,他指向左邊的次數占大多數。
輪到我了。早先,有人低聲對我說,指向右邊表示要工作,指向左邊表示無力工作和有病在身,會被送到一個特別的集中營去。於是,我靜待發落;身上的背袋沉甸甸的,使我稍微歪向左邊,但我奮力站直。挺進隊的這位長官打量了我好一會,似乎在猶豫。而後,他伸出雙手,擱在我肩上,我努力顯出精明的模樣。最後,他非常緩慢地把我扳向右邊,我便向右邊跨去。
當晚,這種「指頭把戲」才告揭曉。原來這是第一次的淘汰與判決──判決我們究竟是生存或喪命。我們那一梯次,約有百分之九十的俘虜被判死刑,而且是在幾個鐘頭之內立刻處決。所有被叫到左邊的人,當時立刻由火車站直接遣送到火葬場。一個在火葬場工作的人就告訴過我,火葬場那棟建築門上,用歐洲各種語文寫著「洗澡間」字樣。進門時,每名俘虜都會收到一塊肥皂,然後──
唉!接下來發生的一切,我不提也罷!反正這種恐怖的事情,許多書刊上都已經報導過了。
我們這些倖存的少數,當晚就獲悉真相。我向幾名曾在那邊工作過的俘虜打聽消息,因為我的一位同行兼好友潘先生被送到那兒了。
「他是被叫到左邊的嗎?」
「對!」我答。
「那麼,你可以看到他在那裡。」他們說。
「哪裡?」我問著,有人伸手指向幾百碼外的一支煙囪。一股火焰,正由煙囪口噴向灰濛濛的波蘭天空,消失在一片不祥的煙霧裡。
「你的朋友就是在那裡,他飄到天堂去了。」我聽了,仍然丈二金剛摸不到頭腦;對方只好用普通的語句另外解釋一次,我這才恍然大悟。
不過,此處所講述的,並沒按照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由心理學的立場來看,從火車站破曉的那一刻起,我們就面臨了一段極其漫長的歷程,一直要等到我們在營中歇息下來,度過第一夜才止。
在挺進隊的警衛持槍戒備之下,我們奉命由火車站穿過通電的帶鉤鐵絲網和營區,奔向清洗站。我們這批通過了第一關的邋遢人,在這兒可以說真正享受到洗澡的舒暢。「緩刑錯覺」也因此再度有了個明確保證,連挺進隊員似乎都和藹可親。可惜不多時,我們看出了和藹可親的原因。這些隊員只要看到我們手腕上戴有手表,對我們便親切有加,並且鼓起如簧之舌,以萬般善意的聲調勸我們把手表交出去。既然我們什麼東西都得充公,為什麼不乾脆交給一個看起來比較和氣的人呢?說不定,有朝一日他還可以幫個大忙哩!我們在一個小房間裡等著,那小房間似乎是消毒間的休息室。挺進隊員出現了,並攤開幾張毯子,要我們把身上一切物品,包括手表、珠寶全扔進去。有幾個俘虜還天真地問說:可否留下一枚婚戒、紀念章,或避邪符什麼的,使得在那兒充當助手的幾個資深俘虜為之發笑不已。到那個時候,每個人差不多都已經知道:一切物品會被搜個精光。
我曾試著向一位資深俘虜吐露我的祕密。我偷偷溜到他身邊,指著我外套暗袋裡的一卷紙說道:「你看,這是一本學術著作的手稿,我知道你會怎麼說。你會說我能夠保住老命已經該謝天謝地,不敢再有非分的奢想了。可是我實在克制不住。我必須不計一切代價保留這份手稿。這是我這輩子的心血結晶。你知道嗎?」
嗯!他是知道了。他臉上慢慢綻出一個笑容,起先帶著悲哀,繼而變成逗趣,而後現出嘲弄和侮辱的表情,最後他以營中俘虜慣用的一個字彙,答覆我的問題:「狗屎!」就在那一刻,我認清了眼前的現實,並且抵達了我第一階段的心理反應的最高潮:我揮手斬斷過去的一切。
突然間,大夥兒騷動起來,一個個臉色蒼白、戰戰兢兢地站著,並且議論紛紛。此時,刺耳的吆喝聲再度響起,我們在哨子的催
促下趕忙跑進堂前的休息室,然後在一個挺進隊員四周集合起來。此人一直等著所有的俘虜統統到齊,才開口說道:「我給你們兩分鐘,並且用我的手表計時。在這兩分鐘內,你們要脫個精光,並且把所有的衣物放在腳板前面。除了鞋子、皮帶或吊帶,或者疝氣帶,其餘全部不准留在身上。我就要計時了──開始!」
大夥兒不假思索,立刻急匆匆地寬衣解帶。時限愈短,每個人就愈形緊張,笨手笨腳地扯著內衣褲和鞋帶腰帶。不久,一陣鞭打聲響起,原來是皮鞭打在赤條條的人體上所發出的響聲。
後來,我們被趕到另一個房間剃毛,不唯頭髮、鬍鬚都要剃掉,連身上任何部位的毛也得剃個精光。接下來便是到淋浴間,大夥兒再度排隊。此時,每個人幾已面貌全非,彼此間差不多都認不出來了。差可告慰的是,有些人發覺蓮蓬頭上的確有水滴下來。
等候淋浴時,全身的赤裸,使得我們認清了一個事實;此際,我們除了這光禿禿的一身,的的確確是一無所有了;就連身上的毛髮,也已經被剃除淨盡,僅餘這赤裸光溜的身體。我們還有什麼物質上的東西,可以同過去的生活產生關連呢?我個人,還有一副眼鏡和一條皮帶,可是隔沒多久,我就不得不用皮帶去換取一片麵包了。擁有疝氣帶的,倒是多了一樣值得慶幸的東西。當晚,管理我們那間茅舍的資深俘虜在致詞歡迎我們的時候,就嚴正地警告說,如果有誰膽敢把錢鈔或珠寶縫進疝氣帶內,他一定會親手把那個傢伙吊到屋梁上。說著,他指了指上頭那根橫梁,並且驕傲地說他資格老,按營規他有權這麼做。
說到鞋子,事情可沒這麼簡單。我們雖然有權保留鞋子,但擁有適腳鞋的人,最後都不能不予以放棄,換來一雙不適腳的。更苦惱的是,有些俘虜聽從了資深俘虜在休息室內的善意忠告(表面上似乎是善意的),便把過膝長統靴的上半截切掉,並用肥皂塗去切痕,藉以掩飾。可是,挺進隊長似乎早就料到了這一招,因此每個有嫌疑的俘虜都被叫到隔壁一間小屋裡。不久,皮鞭的呼嘯聲和挨打者的號叫聲隔牆傳來,而且持續了好一陣子。
某些人心中尚存的幾個幻想,就這樣逐一歸於破滅。意外的是,大多數人心頭漸漸滋生出一股頑強的幽默感。我們知道,除了這可笑的赤裸之身,我們已別無他物可供喪失。當蓮蓬頭開始噴水,我們全都努力地尋開心,努力開自己和彼此間的玩笑。畢竟,蓮蓬頭總算還噴得出水來哩!
除了那股奇特的幽默感,我們的心頭另外還蟠踞著一種感覺;好奇心。這種好奇心我以前也體驗過,那是我碰到某種奇特境遇時的一個基本反應。每當我遭逢意外、處境危險,在緊要關頭之中,我所感到的只是好奇。我想知道自己究竟能全身生還,或者負傷而歸。
即使在奧殊維茲,冷靜的好奇心仍然凌駕一切,使得理智能超越周遭的環境,進而以客觀的眼光看待周遭。在當時,培養這種心境,是為了保護自己。我們急於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而且後果又會怎樣。譬如,當我們淋浴完畢,身體赤裸而猶濕,卻要站在戶外忍受著晚秋刺骨的寒意;當其時,每個人對下一個「節目」就十分好奇。往後幾天,這種好奇漸漸轉變成驚訝:驚訝於自己居然沒有感冒。
大凡新到俘虜,總有一籮筐類似的驚奇等著他去發掘。如果他是醫科出身的,那他一定最先發現教科書全是在扯謊!譬如,我就記得教科書上說過:人如果每天沒有睡滿一定的鐘點數,就活不下去。這真是大謬不然。過去,我一直深信有些事我就是辦不到或無法適應;比如,我沒有某樣東西就睡不著,我沒法跟某種人或某種現象共處於同一個屋簷下。可是在奧殊維茲的第一晚,卻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們睡的是一層層搭架起來的硬木板床。每張床寬約六呎半到八呎,卻擠了九條大漢,而且九個人分蓋兩條毯子。當然,我們只能側臥且彼此緊挨著身子。這樣倒有個好處,因為天氣實在太冷了。
按規定,鞋子是不准帶上床的,不過,有些人還是偷偷把沾滿泥垢的臭鞋墊在頭下當枕頭,免得都快脫臼了的手臂,還要為「曲肱而枕之」而受罪。怪的是,睡神依舊光臨,讓大家在黑甜的夢鄉裡得到幾個小時的解脫。
還有些我們居然都能忍受的境遇,也值得一提。我們無法刷牙,維他命又嚴重缺乏,奇的是,每個人的牙齦,反而遠比以前健康。同一件襯衫,我們得穿上半年,直到毫無襯衫樣為止。由於水管凍結,我們常常一連好幾天不能洗澡(即連局部沖洗也不行),然而手上擦傷發炎之處,卻不因為工作得滿手污垢而化膿(當然,凍瘡則又另當別論)。還有像淺眠易醒者,以前只要隔壁稍有輕響,立刻會驚醒過來,如今身邊緊挨著一個鼾聲如雷的傢伙,卻睡得香甜萬分,絲毫不受干擾。
杜斯妥也夫斯基曾斷言:人無論任何境遇,都適應得了。現在,如果有人問我這句話究竟對不對,我會說:「對!人什麼都適應得了,不過別問我怎麼適應的。」只可惜,心理學研究目前還沒進展到那個地步;我們俘虜在當時,也還沒達到那個境界。當時,我們仍處在心理反應的第一階段。
每個人差不多都有過自殺的念頭(即使為時十分短暫)。這是由於境遇的無望,無時無之、無日無之的死亡威脅,以及目睹他人慘死的驚懼使然。我基於個人的信念(此容我稍後再述),在營中的第一晚就私下作了個堅決的許諾:我絕不去「碰鐵絲網」。「碰鐵絲網」是集中營裡流行的一句話,意指最常見最普遍的自殺辦法──去碰充有電流的帶電鐵絲網籬笆。我下這個決心,並不算太困難。自殺可以說毫無意義,因為,一般的俘虜只要客觀地估計,且算好一切可能的良機,都會發覺活命的指望極其渺茫。他無法自信能通過連番的淘汰,因為通得過的人實在是少之又少。奧殊維茲的俘虜,在滿懷驚駭的第一階段當中,並不怕死,經歷過最初幾天之後,連煤氣間的恐怖也不足畏了。
我後來遇到的幾位朋友,都告訴我說,入營時那種驚駭,我的還不算特別嚴重。因為,在奧殊維茲度過第一夜後的翌晨,發生了一個插曲;當時,我只是笑笑,而且是由衷的一笑。事情是這樣的:我有個同業,比我早到了幾個星期。當局雖嚴禁擅離屬區,這位仁兄還是偷偷溜到我們營舍,想安慰我們,並告訴我們一些事。他變得實在太憔悴,我們好不容易才認出他來。他擺出高度的幽默和滿不在乎的姿態,匆匆關照我們:「別怕!也別擔心被淘汰!馬醫生(挺進隊的醫科主任)對醫生特別照顧。」(這話其實有錯。一位六十多歲的醫生俘虜就告訴我,他曾經哀求馬醫生放過他那個被送往煤氣間的兒子,馬醫生無情地拒絕了。)
「不過,請你們牢記一點,」他繼續說道:「如果可能,最好每天修臉。即使用玻璃片來修……或即使用你們僅餘的一片麵包來換取修臉機會,都大大值得。修了臉,看起來比較年輕,臉色也比較紅潤。如果你們想活命,唯一的辦法便是:擺出還能勝任工作的樣子。如果你只是跛腳──譬如說,你腳跟起泡,不幸被挺進隊員發覺,他會把你叫到一邊,然後第二天送你到煤氣間。你們知道我們所謂的『末世臉』(Moslem,原意為回教徒)是什麼意思嗎?一個人如果臉色黯淡、形容憔悴,一副病懨懨的樣子,而且無法再勝任吃力的苦工……這人就是個『末世臉』。遲早──通常是快得很──他就會進入煤氣間。所以千萬記住:時常修臉,走路或站立都要挺直腰桿。這樣就不必怕煤氣間。你們這幾個雖然只在這兒待了一天,卻都不必怕煤氣間,除了你──」他指著我,說道:「請恕我直言。」然後又對其他人強調,「你們中,只有他才該害怕下次的淘汰,所以,不必擔心!」
當下我笑了。此刻,我相信任何人當時如果碰到我這種情況,反應也會和我一樣。
無試讀內容